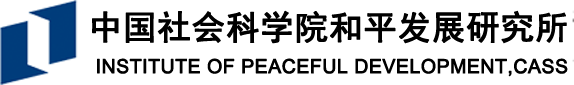2007至2008年的西方金融危机是自1931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但是它的直接影响却出乎意料的温和。这场危机挑战了长期以来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的基石,但后者几乎毫发无伤地摆脱了困境。银行获得了救助,在大西洋两岸的欧美国家,几乎没有银行家被起诉,而他们造成的损失不出意料地落到了纳税人身上。随后,这些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经济政策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货币政策,特别是量化宽松政策,这些政策已经宣告失败。西方经济陷入停滞,几乎是“失去的十年”,而前方出路仍然遥不可期。
 特朗普希望回到20世纪50年代新自由主义发展之前的美国 图源:H.Armstrong Roberts/Getty Images
特朗普希望回到20世纪50年代新自由主义发展之前的美国 图源:H.Armstrong Roberts/Getty Images
经过近九年的时间,我们终于开始品尝到金融危机的政治恶果。新自由主义未能通过现实世界的考验,导致了七十年来最糟糕的经济灾难,但无论政治上还是思想上它仍然是舞台上的唯一主角。为何新自由主义可以毫发无损地生存下来?无论是左翼、右翼还是中间派都接受它的思想哲学,英国新工党便是典型案例。政客们除了新自由主义,就没有其他的思维或处事方式: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所说,它(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某种常识。新自由主义曾独霸一方,但这个霸权未能经受住现实世界的考验,已经无法继续生存。
在众多的政治后果中,第一个现象是公众对银行、银行家和商界领袖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几十年来,这些商政精英被认为“不会犯错”:他们被誉为时代的楷模;被默认是能解决教育、医疗和几乎所有问题的人。然而现在他们的光芒在迅速黯淡,政治影响力也大不如前。金融危机削弱了公众对执政精英能力的信任。这标志着一场更广泛的政治危机已经开始。
导致大西洋两岸这场政治危机的原因,远较单纯的金融危机和过去十年间事实上流产的经济复苏计划来得深刻。而深究这一问题,需得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的新自由主义的核心,里根和撒切尔的政治崛起,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商品、服务、资本的全球自由市场。英国于1986年、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先后废除了大萧条时代确立的银行监管体制,从而为2008年的危机创造了条件。平等观念遭到蔑视,“涓滴经济学”受到称赞,政府被批评束缚了市场,因而缩减规模。移民受到鼓励,监管制度被减少到最低限度。税收削减,企业逃税也被刻意忽视。
应该指出的是,按历史标准衡量,新自由主义的表现并不突出。战后西方经济增长最活跃的时期是从二战结束一直到70年代早期,那是福利资本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时代。当时的增长率是1980年至今的新自由主义时期的两倍。
 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迎来自由主义时代,拍摄于1984年 图源:Bettmann Archive
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迎来自由主义时代,拍摄于1984年 图源:Bettmann Archive
但迄今为止,新自由主义时期最具灾难性的特征是不平等现象的急速增长。直到不久前,这个问题才开始得到重视。在极短的时间内,不平等问题已经成为大西洋两岸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至少是在美国。它以无与伦比的力量促生社会不满,席卷西方政治。在统计数据面前,人们困惑而震惊:这个问题竟被忽略了如此之久;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新自由主义及其价值观处于霸权地位。
但如今,现实击碎了新自由主义的虚幻外壳。在1948至1972年间,各阶层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都经历了相似且大幅度的提高;而在1972至2013年间,收入最少的10%人口的实际收入下降,而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财富增速却比其他所有人都高得多。在美国,全职男性工人实际收入的中位数比四十年前还低,收入较低的90%人口的收入增长停滞超过30年。
英国的情况也基本类似。自金融危机以来,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平均而言,从2005到2014年,25个高收入经济体中,65-70%的家庭实际收入都陷入停滞甚至下降。
原因不难解释。这个高度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全面而系统地朝资本而非劳动力倾斜——国际贸易协议基本都是秘密签订的,只有企业参与其中,而工会和公民被排除在谈判之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就是最近的例子;工会受到政治和法律的双重攻击;美国与欧洲鼓励大规模移民,这削弱了国内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对失业人员也没有实质性的再就业培训。
如托马斯·皮克迪(《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作者)向我们揭示的,在缺乏(反补贴压力)约束的情况下,资本主义自然倾向于增加不平等。从1945到70年代末,冷战竞争可以说是对资本主义最大的约束。但自苏联解体以后,就再也不存在这样的约束了。然而随着民众的反对日渐增长,无可遏制,这种“赢家通吃”(winner-takes-all)的制度在政治上已变得不可持续。
如今,英美两国都有大批人开始反抗被分配到自己头上的命运。美国人对特朗普和桑德斯的热情支持,以及英国脱欧公投获得成功,都明确体现了这一趋势。这种普遍的抗争被描述为民粹主义。就像福山最近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中描述到,“‘民粹主义’是政治精英给他们不喜欢的、但普通民众支持的政策贴上的标签。”民粹主义是改变现状的运动。它代表了新事物的开始,然而民粹主义反对性远大于建设性。民粹主义可以是进步的,也可以是保守的,但通常情况下它兼而有之。
英国脱欧就是民粹主义的典型例子。它颠覆了英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政策传统。这表面关乎欧洲,实际上牵涉诸多:许多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生活水平就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在无法控制的大规模移民潮中,他们就业受到临时工威胁,岗位越来越不安全,感到慌乱、被时代抛弃,他们因此开始大声疾呼、强烈抗议。他们的抗争震惊了执政精英,一位首相(暗指卡梅伦)已经因此辞职,接任者还在一筹莫展地摸索应对之策。
 英国脱欧标志着工人阶级的抗争 图源:MarkThomas/Alamy
英国脱欧标志着工人阶级的抗争 图源:MarkThomas/Alamy
民粹主义的浪潮标志着在政治活动中阶级重返政治核心,无论是在英国还是美国都是如此。这种现象在美国尤其具有标志意义。几十年以来,“工人阶级”在美国政治话语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大多数美国人将其自身定义为中产阶级,这是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在2000年仅有33%的美国人将其自身定义为工人阶级,到了2015年数字飙升到48%,几乎覆盖美国一半人口。
英国脱欧,也是工人阶级反抗的体现。迄今为止,阶级在欧美政治中的角色一直在消退,让位于性别、种族、性取向、环境等有关问题。阶级有其强大的影响力,故而阶级的回归有潜力去重塑政治格局。
阶级的再度出现不能简单等同于劳工运动。二者定义不同:这点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英国也日渐尤甚。事实上,过去的半个世纪以来,英国的阶级和劳工运动之间的差别日趋显著。在英国,工人阶级作为一种政治声音再度出现,在英国脱欧过程中表现最为明显,它被看作是愤恨和抗议的早期表达,只有极弱的属于劳工运动的意义。
事实上,在形成对移民、欧洲问题的现实立场方面,英国独立党与工党同等重要。在美国,特朗普和桑德斯都提及工人阶级反抗,后者提的不比前者少。工人阶级不属于任何人:与左翼人士惯性的认知不同,工人阶级的政治倾向是个变量,不可预先设定。
新自由主义的时代正从两个方面被削弱。一方面,如果说过去经济增长表现不够强劲,如今却更加低迷。欧洲经济增长几乎与2007年金融危机前夕持平;美国虽然表现更好,但其增长也非常疲软。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预测未来经济很可能陷入长期停滞。
更糟糕的是,经济恢复疲软且脆弱,人们普遍相信另一场金融危机将会卷土重来。换句话说,新自由主义时代将西方带入了上世纪30年代那种危机深重的世界。在此背景之下,不足为奇的是,大部分西方人认为他们的孩子会比他们生活水平更糟。另一方面,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已经失利落后的人们不会默认他们的命运,他们会更加公开地反抗。我们正在见证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终结。它还没有死亡,但却处于濒临消亡的早期,就像20世纪7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那样。
知识分子越来越反对新自由主义,这是其影响力减小的显著信号。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经济讨论的焦点被货币主义者和自由市场论者把持。西方金融危机以来,专家学者争论的重心发生了深刻改变。这点在美国体现最为明显,例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保罗·克鲁格曼, 丹尼·罗德里克和杰夫瑞·萨克斯等经济学家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托马斯·皮克迪的《21世纪资本论》成为了畅销书。他的作品,以及托尼·阿特金森和安格斯·迪顿的作品将不平等问题推上了政治议程的首位。在英国,张夏准,这位在经济学领域被长期孤立的教授,与那些认为经济学只是数学分支的人相比,拥有了更多的支持者。
 没人预见到科尔宾的胜出,拍摄于北伦敦的集会 图源:Daniel Leal-Olivas/AFP/GettyImages
没人预见到科尔宾的胜出,拍摄于北伦敦的集会 图源:Daniel Leal-Olivas/AFP/GettyImages
与此同时,那些先前竭力鼓吹新自由主义的人,例如拉里·萨默斯和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如今都极力批评新自由主义。如今批判新自由主义的风声愈吹愈烈,新自由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节节败退。在英国,媒体和政治世界的反应落后于时势的变化。只有极少数人意识到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末期。陈旧的态度和假设依旧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在BBC的“今日”栏目上,还是在右翼媒体或者工党议会都是如此。
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辞职之后,几乎没人能够预料杰瑞米·科尔宾能够在随后的领导人选举中获胜。当时的预测大同小异,都认为一个布莱尔主义者或者如米利班德一样的过渡者会获胜,没人觉得科尔宾会胜选。但是时代思潮在变化。工党党员,尤其是以空前规模加入工党的年轻党员,他们期待一个全然一新的工党。由于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派不同程度地信奉新自由主义和超级全球化,导致左派无法成为幻想破灭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失去了崛起的机会。这一现象最极端的表现是以托尼·布莱尔为首的英国新工党和以比尔·克林顿为首的美国民主党,他们在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先锋代表,提出了“第三条道路”。
但正如戴维·马昆德在《新政治家》杂志中评论道,如果一个社会民主党派不代表那些贫穷者、弱势者和失败者,那么它的意义在哪儿?新工党抛弃了需要它的人们,那些传统意义上它所代表的人们。那么那些曾被新工党抛弃的人们如今抛弃新工党,这又令人吃惊吗?布莱尔下台之后由于痴迷金钱而为别国名声不佳的总统和独裁者当顾问,这简直是新工党消亡的最佳佐证。
科尔宾的竞争对手,伯翰、顾绮慧以及肯德尔,代表着旧政的延续。科尔宾赢得60%的选票,压倒性地击败了他们。新工党就此完蛋,就像蒙提·派森(英国一个著名的六人喜剧团体——译注)的那只鹦鹉一般死得透彻。但是很少有人领会所发生事情的意义。《卫报》发表的社论对工党党员的增加表示欢迎,并呼吁支持顾绮慧,正好浇灭支持者的热情。而议会工党则拒绝接受科尔宾当选的结果,并竭尽全力除掉他。
工党当初化了太长时间来忍受20世纪70年代撒切尔主义的兴起与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现在它仍然无法掌握撒切尔模式,最后只好以新工党的名义拥抱它,才算是上了轨道。工党与其它政党一样必须更新思维。那些反感新工党的党员转而支持从来没有接受过新工党政策的科尔宾,而科尔宾在任何方面都是布莱尔的极端反面,浑身上下散发出布莱尔明显不具备的真实和正派。
科尔宾不属于新时代,他仍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他没有受到新工党遗产的污染,因为他从来就不曾接受过它。但是,他似乎也不理解新时代的性质。危险之处在于,在一个高度不稳定、无法预测的政治环境中,他是深陷其中的泥足巨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安定感。在这种情况下,工党发觉自己处于危险的分裂和脆弱状态。
工党或许正在接受深度治疗,但保守党的状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戴维·卡梅伦在脱欧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不负责的误算,他难辞其咎,不得不在最不光彩的情况下辞职。保守党无可救药地分裂了。脱欧之后,它不知道该向何处去。脱欧派描绘了一幅英国摆脱衰落的欧洲市场,拥抱扩张中的世界市场之后的乐观画面,但是他们没有点明他们心目中的世界市场包括哪些国家。看起来,新首相有一种不合时代潮流的对中国的敌意,有意抹杀乔治·奥斯本做出的不懈努力。如果英国政府背对中国这个目前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市场而行,它又能转向何处?
脱欧让国家处于分裂,苏格兰选择独立的前景变得真切。保守党似乎还没有感觉到,新自由主义时代正在垂死挣扎。
 在克利夫兰,特朗普再次强调“美国优先” 图源:Joe Raedle/GettyImages
在克利夫兰,特朗普再次强调“美国优先” 图源:Joe Raedle/GettyImages
英国发生的事情如此具有戏剧性,但它们仍然无法与美国发生的事情相提并论。特朗普横空出世,赢得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不但搞懵共和党,也搞懵了所有空谈家。他传达的信息简单直白,就是反对全球化。他相信工人阶级的利益被大公司牺牲掉了,大公司受到激励在全球投资,由此剥夺了美国工人的工作岗位。不止如此,他声称大规模移民削弱了美国工人的谈判地位,拉低了他们的工资水平。
他提议,应当要求美国公司投资本土。他相信《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结果是将美国工作岗位出口到了墨西哥。基于类似的理由,他反对TPP和TTIP。他也批评中国盗走了美国工作岗位,威胁要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征收45%的关税。
针对全球化,特朗普提出了他的经济民族主义:“把美国放在第一位”。他总的来说是在投白人劳工阶级之所好。直到特朗普以及伯尼·桑德斯登上美国政治舞台,美国的白人劳工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被忽视,在政治上无人代表他们。过去的40年中,他们的工资一直在减少。政治人物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忽视他们的利益,这真是令人震惊。他们越来越多地投票支持共和党,但是共和党早就被超级富豪和华尔街把持,后者都是亢奋的全球化支持者,他们的利益一直与白人劳工阶级背道而驰。特朗普出现后,劳工阶级终于找到代言人:正是他们帮助特朗普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伯尼·桑德斯也狂热地追捧经济民族主义主张。他在竞争民主党内候选人提名时与希拉里·克林顿只存在很小的差距,要不是所谓的700名超级代表,他很可能就赢了。这些超级代表是由民主党的提名机制选出来的,一边倒支持希拉里·克林顿。民主党人虽然依靠贸易工会起家,但也与共和党一样一直支持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战略。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现在发现他们各自党内都因支持或者反对全球化,出现极度撕裂。这是自里根总统40年前当政,美国转向新自由主义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进展。
特朗普的另一个民族主义主张“让美国再次强大”代表了他的外交政策立场。他相信美国追求大国地位浪费了国家资源。他认为美国的同盟体系不公平,美国在其中承担了大部分的成本,他以日本和韩国以及北约的欧洲成员为主要例子,指责盟友承担太少太少。他要求重新平衡这些关系,如果做不到,就退出同盟。
他主张,美国作为一个衰落中的国家承受不起维护同盟的财政支出。他指出美国的基础设施破败不堪,与其维护世界公义,不如把钱投向国内。特朗普的立场代表了对美国充当世界霸权的重大批判。相对于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和狂热全球化意识形态,以及战后以来一直居于“正统”地位的美国外交政策,特朗普的立场是同它们的激进决裂。需要严肃对待这些表态,不能因为这些表态来自特朗普而忽视它们。但是特朗普不是左派,他是右翼民粹主义者。他对穆斯林和墨西哥人发动了种族歧视和仇外攻击。特朗普要讨好的是白人劳工阶级,这些人觉得自己被大公司欺骗,被拉美裔移民暗害,仇视其认为低人一等的非洲裔美国人。
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可能意味着滑向极权主义,滥权、寻找替罪羊、歧视、种族主义、独断专行以及暴力可能成为其特色;美国可能成为一个深度分化,严重割裂的社会。他威胁要对中国征收45%的关税,一旦实施,注定招致中国的报复,迎来一个保护主义时代。
桑德斯输掉了民主党内的提名,特朗普很可能重蹈覆辙输掉总统大选。但是这不意味着反对超级全球化的势力会放弃自己的观点,偃旗息鼓。美国社会仍然会就不受限制的移民、TPP和TTIP、资本自由流动以及类似议题继续争论。在短短12个月的时间内,特朗普和桑德斯改写了这场大论战的性质和条件。大约三分之二美国人同意:“我们不应当对国际事务考虑得那么多,而应当更多地关注我们国家的问题。”总之,不平等问题将继续推动反对超级全球化的力量前进。
(文章编译自作者Martin Jacques博客中刊出的全文The death of neoliberalism and the crisis in western politics)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所版权所有
京ICP证040743号 京公安网备11010802011033 Copyright©1999-2015 ipd.cssn.cn Inc. All rights reserved.